

城内迁居导致的街区尺度人口动态变化测度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武汉市实证
|
牛强(1978— ),男,湖北武汉人,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为大数据分析、信息时代的城乡规划、定量城市研究和规划分析等研究。E-mail: niuqiang@whu.edu.cn |
收稿日期: 2023-11-28
修回日期: 2024-02-1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8-2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278075)
Measurement of neighborhood-scale population dynamic changes due to intracity migration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Wuhan City based on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Received date: 2023-11-28
Revised date: 2024-02-19
Online published: 2024-08-22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52278075)
准确把握城市内部人口动态变化规律,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社会空间结构。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尺度的人口总量及分布变化,对于城内迁居导致的人口动态变化过程缺乏关注,其测度方法、特征规律等尚待探讨。论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以武汉市为例展开实证分析,构建人口动态变化的“规模—方向—动静”三维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聚类分析方法,解析城内迁居带来的街区尺度人口动态变化特征,探究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及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心城区到近郊区的人口动态变化具有“高活跃→中活跃→非活跃”的规模特征、“出入大致平衡→严重失衡”的方向特征以及“静态为主→动态为主”的动静特征;② 武汉都市发展区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共有5类,其中高活跃增长动态型和高活跃流失弱动态型主要穿插分布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组团的核心区,中活跃微流失弱动态型主要分布在上述两类的外围,低活跃微增长强动态型与低活跃平衡动态型分布于中心城区边缘和近郊区组团外围;③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具有“中心—外围”嵌套结构,中心城区与近郊区之间人口动态变化的空间分异主要与区位、居住环境品质有关,中心城区内部、近郊区组团内部的空间分异则主要与产业发育及类型有关。研究拓展了人口迁移和人口变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为优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精细化制定居住空间供给政策等提供了参考依据。
牛强 , 胡金鹏 , 梁晓倩 , 刘晓阳 , 伍磊 . 城内迁居导致的街区尺度人口动态变化测度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武汉市实证[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8) : 1481 -1495 . DOI: 10.18306/dlkxjz.2024.08.002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patterns of population dynamics within cities can help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optimize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ociety.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changes at the macro scale, but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dynamics caused by intracity relocation, and its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yet to be explored. Based on cell phone signaling big data and taking Wuhan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carried ou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indicator system of scale-direction-movement for population dynamics, applying cluster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dynamics at the neighborhood scale caused by intracity relocation, and exploring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dynamics changes and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opulation dynamics from the central city to the suburban areas have the scal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y active→moderately active→inactive, dire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oughly balanced in and out→seriously imbalanced, and dynamic/static characteristics of static-oriented→dynamic-oriented. 2) There are five comprehensive types of population dynamics in the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of which the highly active-growth-dynamic type and the highly active-loss-weak dynamic type are mainly interspersed in the core areas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and the suburban area clusters; the moderately active-slight loss-weak dynamic type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above two types; and the inactive-slight growth-strong dynamic type and the inactive-balance-dynamic type are distributed at the edge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and the suburban area clusters. 3) The comprehensive types of population dynamics within the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have a core-periphery nested structur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opulation dynamics betwee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and the peri-urban areas is mainly related to lo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ith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opulation dynamics between the central city and peri-urban areas is mainly related to lo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central city and peri-urban areas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type of industries. This study expanded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change,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soci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society, and for fine-tuning the policy of residential space supply.
表1 人口动态变化测度指标体系及说明Tab.1 Population dynamic change measurement indicator system and description |
| 指标维度 | 指标符号 | 指标名称 | 计算公式 | 指标含义 |
|---|---|---|---|---|
| 规模 | 迁入规模 | — | 研究单元人口迁入的活跃程度 | |
| 迁出规模 | — | 研究单元人口迁出的活跃程度 | ||
| 总迁移规模 | 研究单元总迁移的活跃程度,等同于现有研究中的总活跃度 | |||
| 方向 | 净迁移规模 | 研究单元净迁移的活跃程度,等同于现有研究中的净活跃度 | ||
| 迁移平衡度 | 研究单元期末动态迁入人口与基期动态迁出人口的比例 (进行ln函数变换处理) | |||
| 动静 | 动态人口率 | 研究单元期末动态迁入的人口占期末总人口的比例 | ||
| 静态人口率 | 研究单元未发生迁移的人口占期末总人口的比例 | |||
| 动静平衡度 | 研究单元期末动态迁入的人口与未发生迁移人口的比例 (进行ln函数变换处理) | |||
| 动静人口结构 | 研究单元动态迁入与迁出总人口与未发生迁移人口的比例 (进行ln函数变换处理) |
注:n迁入为研究单元迁入人口;n迁出为研究单元迁出人口;n静态为研究单元未发生迁移人口。 |
表2 人口迁移对人口动态变化影响的综合类型划分Tab.2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of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on population dynamics |
| 序号 | 类型 | 网格单元数量/个 | 占比/% | 人口动态变化特征 | ||
|---|---|---|---|---|---|---|
| 变化规模 | 变化方向 | 动静方面 | ||||
| Ⅰ | 高活跃增长动态型 | 506 | 9.59 | 人口高度活跃 | 人口高增长、迁入主导 | 静态人口比例中等、动静结构均衡 |
| Ⅱ | 高活跃流失弱动态型 | 312 | 5.91 | 人口高度活跃 | 人口高流失、迁出主导 | 静态人口比例高、结构偏静态 |
| Ⅲ | 中活跃微流失弱动态型 | 1281 | 24.27 | 人口中等活跃 | 人口低流失、迁出主导 | 静态人口比例高、结构偏静态 |
| IV | 低活跃平衡动态型 | 1753 | 33.22 | 人口低活跃 | 人口动态平衡 | 静态人口比例中等、动静结构均衡 |
| V | 低活跃微增长强动态型 | 1230 | 23.31 | 人口低活跃 | 人口低增长、迁入主导 | 静态人口比例低、结构偏动态 |
| — | 其他 | 195 | 3.70 | 人口不活跃 | 无显著特征 | 无显著特征 |
注:其他类型人口基数小,人口动态变化情况极不显著。 |
图9 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的空间分布Fig.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types of population dynamic change |
表3 各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的典型空间分析Tab.3 Typical space of the comprehensive types of population dynamic change |
| 序号 | 人口动态变化类型 | 不同区位的典型空间卫星遥感影像图(1 km×1 km) | |||
|---|---|---|---|---|---|
| I | 高活跃增长动态型 | 中心城区核心 | 近郊区组团核心 | ||
 |  |  |  | ||
| 汉口:老旧小区 | 鲁巷:产业园区 | 流芳:新建小区 | 吴家山:老旧小区 | ||
| II | 高活跃流失弱动态型 | 中心城区核心,穿插在Ⅰ类型中 | 近郊区核心,穿插在Ⅰ类型中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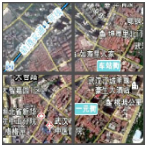 |  |  |  | ||
| 汉口:老旧小区 | 武昌:老旧小区 | 流芳:老旧小区 | 纸坊:老旧小区 | ||
| III | 中活跃微流失弱动态型 | 中心城区核心外围,紧邻I、II类型区 | 近郊区核心,穿插在I类型中 | ||
 |  |  |  | ||
| 硚口:老旧小区 | 杨春湖:居住工业混合区 | 盘龙城:低层住区 | 纸坊:老旧小区 | ||
| IV | 低活跃平衡动态型 | 中心城区边缘 | 近郊区组团外围,城乡结合部 | ||
 |  |  |  | ||
| 汉口:城中村 | 南湖:还建住区 | 蔡甸:居住工业混合区 | 吴家山:村庄 | ||
| V | 低活跃微增长强动态型 | 中心城区边缘 | 近郊区组团产业园 | ||
 |  |  |  | ||
| 汉江湾:还建住区 | 南湖:低层住区 | 常福:产业园区 | 武湖:产业园区 | ||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对本文理论梳理、数据方法、内容组织等方面提出的宝贵意见!
| [1] |
|
| [2] |
|
| [3] |
杜志威, 李郇. 基于人口变化的东莞城镇增长与收缩特征和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 2018, 38(11): 1837-1846.
[
|
| [4] |
尹旭, 王婧, 李裕瑞, 等. 中国乡镇人口分布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22, 41(5): 1245-1261.
[
|
| [5] |
邓楚雄, 李民, 宾津佑. 湖南省人口分布格局时空变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7, 37(12): 41-48.
[
|
| [6] |
修春亮, 王新越. 人口变动的空间分异及其规划学意义: 以哈尔滨、伊春为例[J]. 经济地理, 2003, 23(5): 661-665.
[
|
| [7] |
丁悦, 林李月, 朱宇, 等. 中国地级市间流动人口永久定居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1): 1888-1899.
[
|
| [8] |
甄峰, 李哲睿, 谢智敏. 基于人口流动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南京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22, 41(6): 1525-1539.
[
|
| [9] |
陆希刚, 张立. 区域差异和城乡梯度双重视角下的中国流动人口迁移空间模式[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5): 66-73.
[
|
| [10] |
王婧雯, 朱宇, 林李月, 等. 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改进与新口径下的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3): 464-477.
[
|
| [11] |
王振坡, 员彦文, 程浩岩.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空间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天津市的微观调查数据[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4): 107-115.
[
|
| [12] |
赵美风, 戚伟, 刘盛和.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理[J]. 地理学报, 2018, 73(8): 1494-1512.
[
|
| [13] |
朱宇, 林李月, 李亭亭, 等. 中国流动人口概念和数据的有效性与国际可比性[J]. 地理学报, 2022, 77(12): 2991-3005.
[
|
| [14] |
牛强, 盛富斌, 刘晓阳, 等.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内迁居活跃度识别方法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22, 41(8): 2142-2154.
[
|
| [15] |
赵美风, 汪德根. 基于村域微尺度的人口流动类型空间分异及作用机理: 以云南玉龙县为例[J]. 人文地理, 2021, 36(3): 148-156.
[
|
| [16] |
马志飞, 尹上岗, 张宇, 等. 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规律及其形成机制[J]. 地理研究, 2019, 38(4): 926-936.
[
|
| [17] |
刘盛和, 邓羽, 胡章.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及空间分布特征[J]. 地理学报, 2010, 65(10): 1187-1197.
[
|
| [18] |
刘振, 戚伟, 齐宏纲, 等. 多时期演变视角下中国人口收缩区的识别、空间特征与成因类型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3): 357-369.
[
|
| [19] |
|
| [20] |
|
| [21] |
王桂新, 陈玉娇.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研究, 2023, 47(2): 48-62.
[
|
| [22] |
|
| [23] |
|
| [24] |
|
| [25] |
|
| [26] |
|
| [27] |
牛强, 盛嘉菲, 刘晓阳, 等. 武汉市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空间异质性影响[J]. 地理科学, 2023, 43(5): 860-868.
[
|
| [28] |
牛强, 王思远, 周婕, 等. 近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服务设施配套与职住人口增长关系探究: 基于多源数据的武汉实证分析[J]. 现代城市研究, 2023, 38(4): 33-40.
[
|
| [29] |
朱玮, 梁雪媚, 桂朝, 等. 上海职住优化效应的代际差异[J]. 地理学报, 2020, 75(10): 2192-2205.
[
|
| [30] |
王德, 朱查松, 谢栋灿. 上海市居民就业地迁移研究: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1): 80-89.
[
|
| [31] |
谌丽, 张文忠, 褚峤, 等. 北京城市街区尺度对居民交通评价的影响[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4): 525-534.
[
|
/
| 〈 |
|
〉 |